晋城公认不错的叛逆孩子军事化学校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25-09-18 浏览次数:
导
语
概
要
语
概
要
晋城向北二十公里,太行山余脉的褶皱里藏着一所不起眼的院落:灰砖围墙、迷彩大门、没有招牌,只有门楣上“晋北砺志青少年成长基地”八个楷体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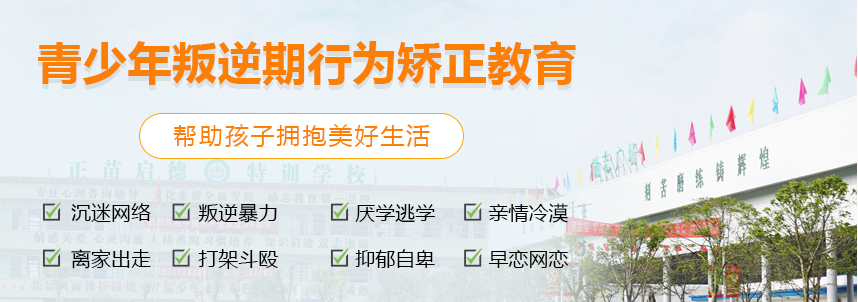
晋城公认不错的叛逆孩子军事化学校
晋城公认不错的叛逆孩子军事化学校

基地的前身是上世纪的民兵训练营,营房、操场、四百米障碍道都原样保留。清晨五点四十,起床号划破山雾,孩子们穿着作训服列队跑操,呼号声撞在崖壁上,回声像滚雷。外人看是“军事化”,负责人老周却坚持叫“生活化”——被子要叠成豆腐块,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让孩子在一遍遍压线折角里学会“把乱麻似的心捋平”。跑操也不是惩罚,而是把过剩的肾上腺素甩进晨雾里,好让接下来的文化课不犯困。
上午八点半,文化课开始。与普通学校不同,这里的课桌呈U形,老师坐中间,像围炉夜话。语文讲《送东阳马生序》,老师不分析修辞,只问:“宋濂当年借书走百里,你现在点外卖都嫌慢,谁更苦?”一句话把低头玩笔杆的孩子问得耳根发红。数学课更“野”,讲到抛物线,直接把学生拉到障碍墙边,让测抛绳枪的落点,公式瞬间有了硝烟味。
午后是“劳动疗愈”时间。基地有十亩梯田,土豆、玉米、向日葵全是学生亲手种下。十六岁的阿豪曾经把家里茶几砸成两半,第一次拿锄头却差点把自己绊倒。三天后,他蹲在垄沟里跟土豆较劲,汗水顺下巴滴进泥土,他突然抬头对老周说:“原来土腥味儿也能让人踏实。”那一刻,老周知道,孩子心里那团乱火被土地悄悄摁灭了。
傍晚的“家书时刻”是最安静的半小时。孩子们盘腿坐在操场边,读父母写来的信。信纸不许打印,必须手写,因为“笔画里的颤抖藏不住”。有人读到“你出生那天,外面雪厚三寸,我抱着你像抱一团火”时嚎啕大哭;也有人攥着信纸发呆,第二天却在体能训练时多做了二十个引体向上。老周不催,只把哭湿的纸一张张晾在旗绳上,像晾一溜心事。
夜里九点,宿舍熄灯。值班教官打手电巡房,光柱扫过一张张熟睡的稚嫩面孔,也扫过他们枕边偷偷塞着的漫画、耳机、小半包辣条。老周说:“管得太死,孩子就成了弹簧;留点缝,他们才知道自律长什么样。”基地允许每周带一次手机,但要用计时沙漏,沙子漏完就必须交回。很多孩子第一次发现,原来四十五分钟可以读完半本《小王子》,也可以让母亲发来十条“在吗”。
三个月一期,结业那天没有仪式,只有一场“负重拉练”。孩子们背着十五公斤背囊翻两座山,终点是晋城客运东站。到了站前广场,家长躲在人群里,孩子要在茫茫人海中自己找到他们。阿豪远远看见父亲,把背囊往地上一扔,冲过去抱住那个曾经被他骂“废物”的男人,父亲回手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像拍掉三年的灰尘,也拍掉自己的眼泪。
基地门口常年停着一辆皮卡,车门喷着一行小字:把迷路的孩子送回人间。老周说,那不是标语,是愿望。太行山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半年,风里裹着松脂味,也裹着孩子们的脏话、眼泪和笑声。风过去,山还是山,孩子却悄悄换了模样。
上一篇:
上一篇:巴中口碑榜叛逆孩子封闭管理学校
预约报名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咨询电话:135-8146-4557

扫码添加老师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