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公认不错的叛逆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25-11-03 浏览次数:
导
语
概
要
语
概
要
眉山多山,岷江穿城而过,水汽氤氲,连脾气也跟着柔和。可再柔的江水也兜不住十四五岁突然炸开的火气:课本撕成雪片,手机砸向墙壁,一句“别管我”把家门摔得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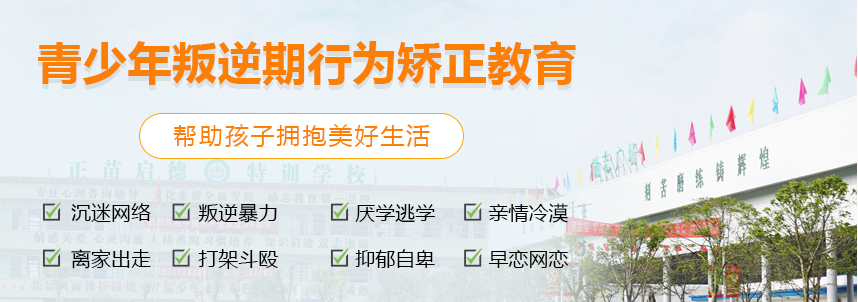
眉山公认不错的叛逆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眉山公认不错的叛逆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基地藏在东坡区一片柚林深处,离市区二十公里,没有铁丝网,也没有高墙,铁艺大门刷成低饱和的灰蓝,远看像民宿。校车停在门口,孩子拖着行李下车,鞋底踩碎枯叶,第一声“咔嚓”就提示:节奏变了。教官不叫教官,叫“成长合伙人”,T恤上印着“先处理情绪,再谈学习”,一句话把身份摁平。
晨跑不是嘶吼着“一二一”,而是放起《青城山下白素贞》,跑调了就被伙伴笑着揽住肩,继续哼。三公里后,汗一出,脸上僵了一路的肌肉先松了。早餐是自助,包子、凉面、玉米、牛奶,自己刷餐盘,水池前两个龙头永远有一个是坏的,于是两人合用一个,肩膀碰肩膀,敌意被水流冲短。
上午的“课堂”更像工作坊:一节“情绪考古”,老师发一张A3纸,让把最近一次爆炸画成地层,最上面是吼出口的话,往下挖是“被拿来跟表弟比较”“爸妈冷战两周”。画着画着,有人把笔一扔,哭得像漏雨,旁边人递纸,不劝,只拍背。哭完,地层自己露出断层,老师才开口:“名字不叫脆弱,叫说明书。”
午后太阳最辣,安排的是“柚林守护”--每人领一棵柚子树,树皮上钉着二维码,扫码录入姓名。少年们蹲在树下拔草,草汁染绿指甲,汗滴进土,第一次发现“照顾”不是作文里的漂亮词,而是喉咙冒烟时仍记得给树浇满二十秒。九月,柚子发黄,基地允许寄一个回家,箱子上手写着“这是我养的”,父母切开,果肉带一点微酸,眼泪比柚子汁先落下。
晚课最特别,叫“盲行”。操场熄灯,一人戴眼罩,一人牵绳,走完五百米弯道。戴眼罩的必须完全交付,牵绳的必须完全负责。轮到小浩牵别人时,他手心全是汗,那个瞬间他突然理解:爸妈的“唠叨”不过是黑夜里的另一根绳。第二天,他主动给家里打电话,开口是:“妈,我昨天带别人走路,没让他摔,你放心。”
三个月一期,结业没有仪式,只在柚林深处挂一块木牌,写着“我在这里把‘别人家的孩子’还给你”。背面是孩子的留言,有人写“柚子熟了,我也熟了”,有人画一只炸毛猫被风吹顺。校车再开回市区,爸妈远远看见,孩子靠窗,耳机分给邻座,阳光斜照,眉宇间那股横冲直撞的戾气被山风重新雕刻成少年该有的锋利与温柔。
上一篇:
预约报名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咨询电话:135-8146-4557

扫码添加老师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