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目前出色的戒网瘾孩子教育学校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25-10-22 浏览次数:
导
语
概
要
语
概
要
赣州的清晨,总被章贡两江水汽轻轻托起,雾气在古城墙头打着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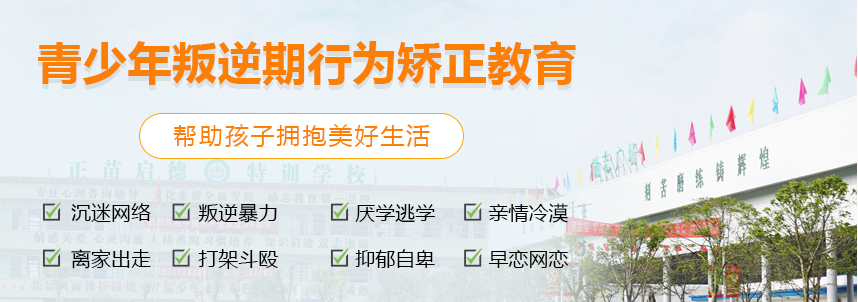
赣州目前出色的戒网瘾孩子教育学校
赣州目前出色的戒网瘾孩子教育学校

创办人赖斌曾是赣州三中的心理老师,十二年前,他因为一次校内危机干预,发现“网瘾”只是孩子递出的求救信号,真正的结扣藏在家庭沟通断裂、学业评价单一、同伴关系塌方里。于是他把心理教研室搬到山脚,带着第一批八个昼夜颠倒打《王者荣耀》的少年,在废弃采石场旁扎帐篷,白天劈柴做饭,晚上围着火堆讲各自最怕的梦。三个月后,八个孩子里七个主动上交手机,不是被没收,而是“想留点力气看看日出”。那轮日出被拍成照片,至今还挂在中心门厅,橘红色像一枚烧红的硬币,把“戒网”两个字烫得卷曲变形。
澄心坚持“三不”:不贴标签、不关禁闭、不强制服药。入学第一步,家长先上课,赖斌把父母请进会议室,关起门来播放他们在家争吵的录音,再让孩子隔着单面镜看见父母红着眼眶写下的“我不知道怎么爱你”。那一刻,玻璃两侧同时响起抽泣,比任何说教都锋利。第二步才是孩子进场,没有体检式搜身,只有一场“十六公里夜行”:沿赣粤古道走到梅林镇,手机装在背包里,允许随时停下拍照,但必须在终点把今天最打动自己的那张洗出来,贴在共享墙上。多数孩子在第十公里就主动关机——“电量要留给拍星星”。第三步叫“还愿”,学生自己设计三个月“小目标”,有人想复原一架航模,有人想给暗恋的女生写一首不押韵的诗,心理老师只当“资源库”,帮孩子拆任务、找工具,让他们在实现过程里重新触摸“我能行”的脉搏。
课程表像一张随机播放的歌单:周一上午可能在菜地测土壤酸碱度,下午就进城给餐馆送菜,顺便把赚来的五十块拿去捐血站,换一张“无偿献血”贴纸;周三深夜会突然被叫醒,去峰山顶录虫鸣,回校剪成白噪音,卖给失眠网友;周五的“家长会”设在浮桥,父母孩子各执一根钓竿,在贡江水面比谁更沉得住气,鱼没上钩没关系,沉默先被水流冲走。基地里唯一被强制锁进柜子的是Wi-Fi路由,每天只在傍晚开放四十分钟,供学生处理网课作业,其余时间,整座校园靠纸质书、乒乓球、旧钢琴和一只叫“路由器”的橘猫打发。令人意外的是,从未出现大规模“戒断反应”,因为日程被好奇与疲劳填满,没空焦虑。
去年,中心走出第两百三十一名学生小宇,他把王者荣耀账号注销前,先给队友发了封长信,说“我要去线下打更大的副本”。今年高考,小宇以598分被江西师大心理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基地那天,他正带着新一届学弟在菜地拔草,满手泥巴接过红信封,第一句话是:“赖老师,明年我能回来当助教吗?”
赣州家长圈里,澄心被称为“隐形重点”,它不对外渲染治愈率,也不拍短视频吸粉,只在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开放二十个参观名额,需要家长先读完《非暴力沟通》并提交三千字笔记。有人笑它“矫情”,可预约号总在十分钟内抢空。傍晚下山时,能看见城外的霓虹一盏盏亮起,那些曾把灵魂寄存在屏幕里的少年,如今踩着滑板或骑着单车,在真实晚风里追逐一只飞得忽高忽低的萤火虫——那一点绿光,像他们重新找回的、对世界的好奇与掌控。
上一篇:
上一篇:延安公认不错的厌学孩子军事化学校
预约报名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咨询电话:135-8146-4557

扫码添加老师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