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公认不错的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25-10-24 浏览次数:
导
语
概
要
语
概
要
嘉陵江拐了个弯,把遂宁城轻轻揽在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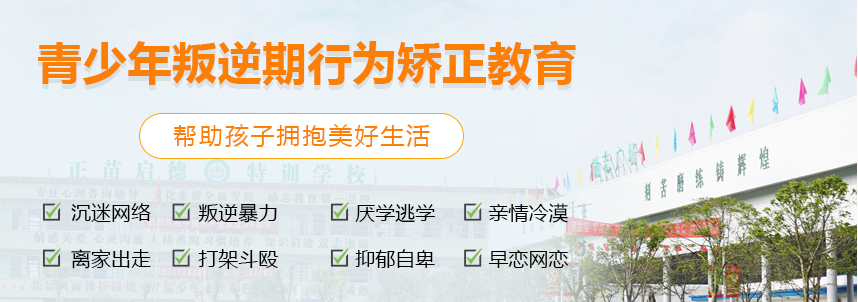
遂宁公认不错的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遂宁公认不错的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

这样的场景,在遂宁并不稀奇。公交车司机老郑能一口气报出五六个“逃学地图”:九莲洲的废弃码头、湿地公园的芦苇荡、圣莲岛尚未完工的摩天轮。孩子们在那里交换电子烟、盲盒卡牌,也交换同一种眼神——对课堂、对家门、对未来的厌倦。
直到去年秋天,老郑在终点站看见一辆没有校徽的中巴,车门喷着淡蓝色海浪,侧面写着“遂宁行知成长营”。司机是个扎马尾的女老师,声音沙哑却带着笑:“师傅,去龙凤古镇,我们‘捡’孩子。”老郑后来才懂,这辆中巴每天巡游,把藏在网吧、桥洞、奶茶店屋檐下的少年“捡”回一座改建的老酒厂——那里墙壁刷成麦黄色,屋顶留着天窗,夜里能看见银河。
酒厂里已经没有酒,只有一排排用旧课桌改成的木工台。林野被“捡”来的第一天,被要求把一块松木刨成平整的“心”形。他故意把刨花撒得满地,老师也不恼,递给他一张砂纸:“你讨厌被磨平,那就让它更毛糙,看看最后扎谁的手。”十天后,那块木头被林野磨得镜面一样,他偷偷在背面刻了“妈妈”两个字。
成长营的课表像一副洗乱的扑克:六点晨跑,七点做饭,八点读诗,九点进车间。车间里没有语数英,只有缝纫机、微型车床、3D打印笔。少年们把对世界的愤怒焊进铁片,把说不出口的道歉缝进布袋。林野给母亲做了一只木簪,簪头刻了嘉陵江的水纹,打磨那天他戴了耳机,放的却是英语听力。
最“吓人”的是周三晚上的“对视课”。孩子们与家长隔着十支蜡烛坐着,不能说话,只能看。林野第一次发现,母亲眼角的细纹像干涸的河床,而母亲也第一次看见,儿子左耳后面有颗星形胎记。蜡烛滴到第三支,两个人同时往前挪了半寸,影子在墙上重叠成一棵小树。
三个月期满,成长营不发毕业证,只发一张“车票”——目的地自己填。有人填“回学校”,有人填“去成都打工”,林野填的是“回家”。他把车票塞进木簪的包装盒,在母亲生日那天清晨,放在餐桌的豆浆碗下。
如今,老郑的公交车又路过那座老酒厂,门口多了块木牌:遂宁行知成长营——允许迷路,也允许回家。夕阳照进来,像一块温热的铜,把“厌学”两个字慢慢熔成“欲学”。林野背书包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耳机里不再是嘶吼的重金属,而是老师录下的嘉陵江潮水声,一浪接一浪,把一座小城的心事推向远方。
上一篇:
预约报名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咨询电话:135-8146-4557

扫码添加老师微信